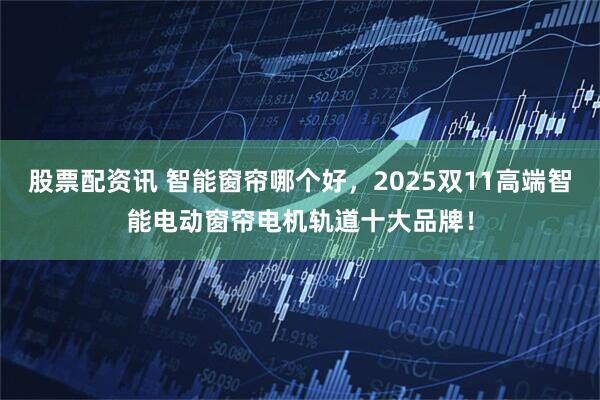连载股票配资讯
作家薛喜君的长篇小说《沾别拉》近期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,作品以沾河林业局“守塔人”为原型,生动再现了四代森工人守护山林、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,是生态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有益尝试。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,我们连载此小说,以飨读者~
作者简介:薛喜君,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,以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见长,出版发行《二月雪》《白月光》等,作品多次获奖。
最慢的是生活
(代自序)
早在2023年11月,我就有了以森工为题材,以森工人为主角,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。当我决定去沾河林业局,体验森工人冬日森林抚育的工作和生活,我最先查询的是动车时刻表。此时,我才知道,那里还没通高铁,经过询问才得知,去沾河有两种选择:汽车、火车。
展开剩余94%我选择了清晨第一班开往沾河的汽车。
雪,是大北方的写照;冷,是大北方的标识。客车刚搭上沾河地界,我眼前就是一片白雪皑皑。司机说,今年冬天的雪太邪乎了,一场接一场,前两天的一场大雪,下得铺天盖地……也就是说,在我来沾河前, 一场大雪刚刚偃息旗鼓。车行驶得很慢,我的心很急,为即将开始创作的文本,还担忧此行能否顺利完成——开座谈会,登瞭望塔,亲身感受瞭望员的日常生活,进山体会森工人冬季的日常工作……我选择出行的日子又是元旦假期。为这,我内心有隐隐的不安。好在沾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杜超,在我到之前,就把行程都安排好了。
下午的座谈会如期举行,与会的森工人深情地讲述了森工发展的历史,并解答了我所要了解的问题。
座谈会后,我登塔的心情十分迫切。
于是,第二天早饭后,我们四人乘车进山。车一出林业局机关的地界,就开始了茫茫的雪野之行。确切说,车不是在行驶,而是在雪窝子里像只蚂蚱似的蹦跶。我的心提了起来,也开始了自责。我没有大山里的生活经验,忽略了山路,还忽略了雪。在我居住的城市里, 一般的雪不会耽误出行,可这是山区啊,山区的雪无法清理。随着车向纵深的雪野行进,山峦也扑进眼帘——我自责得心慌,是我给同行的杜超、于海泳、李恩武添了麻烦。车终于从雪窝子里蹦跶出来,又将从水库的大坝上通过。司机说,某一年,就是我们乘坐的这辆车,在通过这条大坝时,从坝上翻了下去……我的心狂跳起来。我目测, 大坝上的雪至少有十几厘米厚,还是那种光滑得像镜面的冰雪。这条大土坝,比平常的土坝高,距离也长,我紧张得心都快跳了出来。我最先想到的是陪我上山的人。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,不能再让他们陪我冒险……我不敢再想下去。
“掉头回去,不进山了。”这话,我差点儿脱口而出。
车在我紧张得都快窒息的状态下过了土坝。我长长地喘了一 口气。我们终于到了山脚下,打算开车上去。车最终还是陷进了雪窝子里。海泳说,我们徒步上吧。我打头儿,特意穿了一双蹚雪的鞋,裤脚也扎到鞋里——以我的个性,我不会在大雪面前低头。可此时, 我不是一个人。让他们在节日里陪我,我已经十分过意不去。再让他们陪我跋涉于大雪窝子里,登二十四米高的瞭望塔,即便是打着文学创作的旗号,也太过自私了。
“不上,我们就站在这里,遥望瞭望塔。”我果断地说。
我们在山脚下徘徊了许久——我第一次体会到无声的寒冷。风,像刀片似的刮着我的脸,我感受到疼;脚,冻得失去了知觉……杜超、海泳、恩武给我讲述着“天保工程”对森工的意义,讲述着森工人不同季节的工作,讲述着有“森林眼睛”之称的瞭望员对森林的重要性,我一一记在脑子里。
我们要返回驻地,但车罢工了。
我们开始推车,推了二十来分钟,车还是执拗地不肯动。海泳只得从就近的林场叫了一辆车,上山接我们回去。返程中, 我一直在自责——因为无知,所以草率。
回去的路上,我第一次看见在雪野上奔跑着的狍子。
沾河之行,让我大致了解了林业局的历史。我还去了沾河林业局最初的旧址。在座谈会上,我结识了沾河林业局老一辈和新一代森工人。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森工人一路走来的坚韧和不屈。森工的历史长卷是森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写就的。森工人深爱着他们脚下的山水,他们炽热的情感也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我在严寒中感受到了温暖,也体会到了森工人一路走来的疼痛……我离开沾河那天,雪依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。接我来沾河的是杜超,送我返程的还有海泳和恩武。他们还为我买了一袋子吃食,我说我在火车上不吃东西。海泳说,吃着玩,打发时间。
火车上,我不会寂寞,因为有创作要思考。
有人说,绿皮火车是生活,高铁是诗和远方。我深以为然,已经很多年没坐过绿皮火车了,在快节奏的时代里,我也期待着诗和远方。 2024年元旦,我登上了这列从北安开往齐齐哈尔的绿皮火车。我将在鹤城转车,回到我居住的城市。
北安火车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火车站。
双脚一踏上火车的脚蹬板, 一股浓烈的生活气息迎面扑来。顺着过道走到座位前,对面靠窗的是一个年轻女孩,她旁若无人地刷着手机。她身边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妇人,左顾右盼。看到我过来,老妇人不安地欠了一下身子。我的座位也靠窗,小餐桌正是我此刻需要的,挨着过道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男子。
我沉浸于刚刚的分别中,沉浸于即将开始的创作中。
东西放好后,我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,耳边突然传来老妇人的问话:“你今年有五十几了吧,我看你秃顶得厉害。”老妇人的话,让我抬起头。她在与我旁边的男子说话。男子咧了一下嘴,说他没那么大。“那你多大岁数了?我儿子五十八了, 也没你这么秃顶。”男子说他三十八岁。说着话,他把右手抚在额头上,遮挡了半张脸。老妇人往前探着脑袋: “哦,还真没看出来,你才三十八。脑袋秃得太厉害了。”我以为老妇人应该解释一句,可她继续说她儿子的头发比男子的多,还说她到塔哈下车, 儿子开车到车站接她……男子极力想终止对话,但老妇人滔滔不绝,说自己是去儿子家,给孙子带了哪些吃的……其间,老妇人还接了两次貌似是儿子的电话。
挂断电话,她依旧絮絮地说着家里的事儿。
我看向窗外。窗外是被大雪覆盖着的寥落的旷野, 偶尔有村屯掠过,也是稀落的几户人家。雪地上的乌鸦,宛若一朵朵蘑菇;树杈上的乌鸦,像一个个吊着的黑色小布袋……我由衷地感叹,车里车外,都是生活。虽然生活无处不在,但绿皮火车上的生活,是那么真实和悠长。
列车员是一个胖墩墩,五官虽小但对称,还十分喜庆的年轻男子。他拎着一个大黑塑料袋, 一边走,一边吆喝着收垃圾。邻座几个十八九岁学生模样的人,无所顾忌地吃着麻辣烫、方便面、辣条、鸡腿和一些膨化小食品。偶尔,他们也打闹一阵,说笑几句。浓郁的调料味道在车厢里弥漫。“大过节的,你们出来干啥?还以为我这个班能清闲,整了半天,你们都到车上来过节了。”学生们嘻嘻哈哈地笑,把手边的包装袋、包装盒、包装纸,一股脑地扔进列车员提着的那个张着大嘴的黑塑料袋里。
“依安到了。”
随着车厢广播的播报,火车耸动两下,停了下来。 一群背着大包小裹的乘客,潮水般涌进了车厢。咸鸭蛋、干蘑菇、萝卜干、咸菜的味道,汇集在一起,车厢里游荡着浓烈的气息。
生活,在绿皮火车上是缓慢而热烈的。此刻,我突然意识到,慢生活是一种享受,是一种从容。
我置身于车厢的嘈杂之外,又深陷其中。我的心思还没离开沾河,但我又被眼前的慢生活深深地感染着。在来之前,我先拟好了文本的题目,可是到了沾河之后我发现,此前的题目无法表达森工长河一般的历史。我在沾河这几天,沾别拉就萦绕在我的脑子里。就在登上火车时,我终于确定了题目。于是,我在这趟开往鹤城的绿皮火车的小餐桌上,铺开一张便签,写下了“沾别拉”,也写下了“沾别拉是一条河,住在两岸的人都称它为大沾河”。
也就是说,《沾别拉》的开篇,是在 2024年元旦这天的绿皮火车上写下的。
回到我生活的城市,我就开始了创作。创作过程中,我有些焦急,也有些焦虑,因为一代又一代森工人的故事在我脑子里拥挤,我不敢耽搁,怕错过了这些故事。加之公务在身, 一些繁杂的事儿常常打断我与森工人的对话,以至于睡眠障碍再次袭来。由此,我日夜都活在《沾别拉》里。
我感觉到了深深的疲惫。
我在心里说,等完成创作的那一刻,一定给予自己一个奖励。不胜酒力,还不能喝一杯香槟?
眼看龙年春节来了,我深陷于各种杂务的忙碌中,但我没与森工人分别。我终究是累倒了,从没清亮过的喉咙,开始红肿发炎。除夕前一天中午,我还在诊所输液。
春节,我只休息了两天,又开始了创作。
如果没有龙江森工总局及其党委的大力支持,没有沾河林业局的协助,特别是森工总局党委宣传部老部长李玉春、副部长王大明,就没有我的沾河之行,也就没有《沾别拉》。最初,我们针对创作,进行了 一番交流。大明不仅为我提供了资料,简略地讲述了森工各个时期的发展历史,还给我介绍了沾河林业局的丁兆文先生。特别要感谢的是何昌喜老先生。创作过程中,无论遇到什么问题,我都会向他请教。何老先生特别严谨认真,也有文字功底,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,既言简意赅,又深入浅出,使我这个外行都能很快会意。感谢朱彩芹、王刘洋,他们母子的事迹宛若“月老”手里的那根红线,引领我走向森工,走向森工人。这条红线让我找到了《沾别拉》的主人公:杨春洛、高守利、葛丹, 以及杨继业、杨石山、姜占林、曲二手、尤大勺等老一代森工人,也让我找到了以潘望、杨夏璎为代表的新时期森工人……感谢方正林业局的王男,以及方正的森工人,当我有需要,他们都毫无保留地伸出援助的手。
《沾别拉》初稿完成后,我又请何昌喜先生为其纠错。当我说出请求,何老先生欣然接受。读后,何老先生提出了问题,连错别字也在文本上做了标识。也就是说,他是《沾别拉》的第一个读者。
在此,深表感谢!
一
沾别拉是一条河,住在两岸的人都称它为大沾河。
坐落在大沾河左岸的龙镇,被山环水绕,林木繁茂,山野丰盈,居住在这里的人不仅长寿,还友好和睦。人们都说,龙镇是一块风水宝地,一条大直街就在龙脉上。
杨春洛家的祖辈,是龙镇土生土长的坐地户。从祖父杨继业开始,到父亲杨石山,就没离开过龙镇,没离开过辰清林业局。辰清林业局改称山河林业局后,杨家的后人也都是林业人。杨继业一生娶过两房女人,前房女人生了四个儿子,而填房女人姜淑娥一进门,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闺女、一个儿子。杨石山是老小,他一出生,就遭遇了家庭的变故。
父亲杨继业成了一个半截身子的人。
杨继业脑瓜活泛,十分能干。为养家糊口,他倒腾过粮食,为木帮伐过木,拉过“牛马套子”。膀大腰圆的杨继业,一顿能喝二斤烧酒,吃八块玉米饼子,死时两条腿却像是遭遇雷劈了的树杈,成了半截身子的人。和杨继业一起干活的林工,很少叫他名字,都叫他“杨大胆”,或者“杨头儿”。
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,大小兴安岭的资源,宛若一块肥肉,不仅被来自各方的木帮惦记,还被日本鬼子觊觎。他们疯狂地掠夺粮食,对原生红松林更是垂涎三尺,一棵树都不想放过。日本鬼子像是饿急眼的狼,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,对所到之处进行“剃光头”的掠夺式采伐。这还不算,在原生林里,日本人还用“拔大毛”的方式,拣粗壮的树、挺拔的树、枝繁叶茂的树砍伐。他们还主张皆伐。森林,被小日本鬼子祸害得像是长了疖癣,生了斑秃一样。沾河两岸的人恨得咬牙切齿,骂他们不得好死。有人还趁着深夜,烧了日本人存放粮食的仓库,也烧了他们的贮楞场。“一把火烧了狗日的日本鬼子,点他们的天灯!”
日本侵略者也知道中国人民恨他们,但他们仗着有枪有炮,对林工动辄打骂,对百姓更是严加防范。因此,百姓和林工平白无故地消失,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二战末期,日本鬼子溃逃时,要把一片原生红松林化为灰烬,林工们气得自发组织起来护林,杨继业自然成了护林的头儿。 一个日本兵拎着一桶柴油,嚣张地说,他们带不走的东西,宁可毁了,也不给愚蠢的支那人留下。林工们扛着铁锹、木棒、撬棍,与他们对峙。
秋风飒飒,叶子如雨点般飘落下来。就在日本鬼子扬手要把柴油浇到树干上时,杨继业冲上来:“占俺们山,砍俺们木头,临了还要毁俺们的山,灭俺们的林,砍死你们这帮狗杂种!”杨继业举起斧头,怒吼着朝日本兵劈过去,一斧头把拎着柴油桶的小鬼子脑袋开了瓢。刚刚还叫嚣的小鬼子,像一截木头直挺挺地躺下去,油桶砰的一声落到地上。
另一个日本鬼子,看到同伴倒下去,因惊恐而圆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。他红了眼,转手一枪托砸向杨继业。小鬼子的枪托是照着杨继业的脑袋砸的,但杨继业人高马大,枪托砸到了他的胸口处。他脚下正好是一个陡坡,他往后闪躲时,脚下一滑,踩空了,像一根刚伐下来的大树,叽里咕噜地滚了下去。落到山谷时,发出砰的一声闷响。
林工们吼叫着冲过去。一时间,刀斧棍棒的撞击声,谩骂声,鸟儿凄厉的哀鸣声,野兽奔逃时发出的愤怒的嘶吼声,响彻山谷……保住了山林,林工们在布满石砬子的谷底,找到了杨继业。他身子蜷缩,两条血淋淋的腿弯曲着,黑红色的血凝成了冰坨,身上沾满枯叶和灰尘。他被抬回家,林工们直接在仓房里搭了木架子,把他放到木板上。
“准备后事吧。杨大胆死得硬气,死得值,俺们老哥们儿要风光地安葬他。”
刚出月子的姜淑娥,眼眶里饱含着泪光,冷峻地看着林工们,说:“抬
进来,放炕上。就算活不过来,也得让继业的身子舒展开,阴间的道远,还没有亮儿,他佝偻着身子咋走?”
林工们面面相觑,他们从没被一个女人支使过。他们不知所措:“啊,嗯……”
看到林工们像一只只呆鹅,并没有要把杨继业抬进来的意思,姜淑娥脸色凝重地叫过前房的儿子:“杨石、杨磊,带着弟弟,把你爹抬到炕上。”
四个儿子跑到院子里,很快,杨继业被儿子们抬了进来。看到躺在炕头,面色青白得像窗户纸的杨继业,姜淑娥的脸陡然红了,随后又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。手抖了,抽筋了,但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她用一只手掰另一只手,手指终于不再痉挛,她的目光又落到杨石身上。
“老大,去把家里的烧酒都拿出来。老二,把炉子点着,把火墙烧热,再给灶坑架上柈子,别让秋风把炕抽凉。”
两个儿子又跑了出去,再跑进来时, 一个抱着木柈子,一个怀里抱着两个酒坛子。
姜淑娥从线笸箩里拿出一把剪子,细心地剪开男人沾着血污的秋裤,剪开上身的夹袄。没了衣裳裹体的男人,前胸和脊梁骨处露出了多处擦伤,还有几条长短不一的伤口。大腿和小腿处,有几条血口子,左腿腓骨支了起来,右腿膝盖骨塌陷,小腿肚豁开有半尺长的口子,骨肉血淋淋地翻着。左脚的大脚趾翻着,小脚趾不见了踪影。
姜淑娥用一块兰花布盖在男人的腰上,遮住了私密处。她又拿过剃头刀,仔细地刮掉男人脑袋上乱草一样的头发。白皙的头皮裸露出来,脑袋上也有几道伤口,但都不深。
姜淑娥细心地用酒清洗男人身上的伤口,又让大女儿把粗盐粒子碾碎,用开水沏开。被烧酒和盐水清洗后的伤口,露出红红的肉和白刷刷的骨头。男人的身子,让人触目惊心,大女儿吓哭了,但她不敢出声。
儿子们也都低声啜泣。
姜淑娥端起酒碗,仰脖喝下半碗烧酒。辛辣从口腔滑向食道时,心口窝热辣辣的。她用手背抹了一把下颌,又端起酒碗,含在嘴里一口酒,噗的一声喷到男人的脸上。然后,从男人的太阳穴,搓到脖颈,又搓到心口窝,顺着心口窝一寸一寸地往下搓。烧酒让姜淑娥脸色红润起来,再加上她使出全身的力气,气血上涌,她的脸宛若一朵盛开的桃花。站在地上的儿子和林工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儿子们希望爹能在继母手里起死回生。
林工们都觉得她是白费力气。
姜淑娥顾不得投在她身上的期待和怀疑的眼神,恨不能生出一股神力,把男人从阎王爷的手里拉回来。
“继业,回家喝酒。继业,回家喝酒啊……”姜淑娥边搓男人的身子,边低声地召唤。她像是一个母亲,给受到惊吓的婴儿叫魂儿。她的声音温柔得像一只寻找被窝的猫,也像婴儿唤奶时的呢喃。
姜淑娥的额头,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,身子也开始摇晃。从男人被抬进来,她没掉一滴眼泪,前一窝、后一块的儿女齐刷刷地站在地上,只有三岁的小女儿吓得缩在炕脚。出生才一个多月的杨石山,仿佛也知道家庭的变故,一双红红的小眼睛虚无地望着房笆, 一会儿睡了过去,一会儿又醒了过来。
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,扑通跪到地上:“妈——”
二
一场稀稀落落的清雪飘下来。龙镇,就有了肃杀之气。杨继业被抬回来时,天还阴沉着脸,晌午一过,天上的乌云就朝着西边翻滚过去。
龙镇明亮了,光芒齐刷刷地从木格栅的窗户穿透进来。
光,毫不吝啬地打在躺在炕上的杨继业身上, 一张毫无生气的脸上就有了暗影。光也把女人笼罩住, 她的脸就如同打了腮红。“老大老二别跪着,也别哭,上炕,用热盐水为你爹搓脚。”姜淑娥的声音像落在地上的钉子,发出铮铮的响声。杨石跑到外屋,端了一盆热盐水。兄弟俩跪到炕上, 一人抱住爹的一只脚,为爹搓脚。
“使劲——有多大劲都别留着,把吃奶的劲使出来。”
一壶又一壶烧酒,一盆又一盆热盐水,游走在杨继业身上。开始,姜淑娥还坐着搓,后来,她就气喘吁吁地跪在炕上搓。汗水从她的头发里钻出来,把她的头发打成绺儿,又从额头流到脖子上,噼里啪啦地落到炕上。她被汗水泡上了。汗水和男人身上流下来的烧酒、盐水混合到一起,湿透了她的裤子。
太阳开始西沉,天渐渐地暗了下来。山里的夜,来得早。而今天的夜,有些迫不及待。
眼看着姜淑娥支撑不住了,大女儿和二女儿爬上炕,坐在她身后,用后背支撑着母亲。杨继业被揉搓得冒出了一丝热气,身子也渐渐地舒展。姜淑娥宛若一头拉磨的驴,细心地耕着这块她既熟悉,此时又十分陌生的土地。
“哼——嗯——”
姜淑娥终于听见了微弱的喘息声,她停住了手,扭头看男人。脸色如白纸的杨继业,依旧不声不响地闭着眼睛。她想可能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,她继续搓。“嗯——哼——哼——”姜淑娥竖起耳朵,像是听到了从遥远的天边滚过来的雷声——确定声音是从男人嘴里发出来的,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姜淑娥跪在炕上,双手推搡着杨继业:“继业,你活了!继业——,你活了!俺们娘儿们有救了,继业啊——”她匍匐到炕上,悲痛地号哭。在外屋抽烟打盹的林工们,听见屋里女人的哭声,纷纷跑进来。
“大胆走了?杨头儿走了?俺们就说你救不活他,山谷那么深,摔下去咋能活?要是活了,真就是老天爷开眼了。”
“我爹没死,他活了。”杨石眼神里有惊喜,也有恐惧。
姜淑娥手抚在男人的心口上,她听到了他的心跳声。虽然微弱,却像是听到来自冰层下的流水声。“我就说你不能死,我就说你不能死嘛。你咋会那么容易就死了呢?你不光胆子大,还离不开俺和孩子。”姜淑娥又哭又笑地推搡着杨继业。
杨继业缓缓地睁开眼睛,又闭上,眨巴两下,又睁开:“山火着了,还有救吗?”
杨石泪流满面地摇头:“爹,山火没着起来,正好有一群拿枪的人经过,打死了日本鬼子。他们说,他们是抗联三军的队伍,他们刚在冰趟子那儿打了一场大胜仗,把日本鬼子打得哭爹喊娘。”
“哈——啊呀——”杨继业想笑,却痛苦地呻吟了一声。
杨继业活了,守在他身边的林工们都流下了眼泪。 一起干活的林工们还不忘嘲笑他,说:“你这家伙,死也离不开烧酒,离不开女人。要不是你女人和烧酒,俺们都给你埋到西山坡了,明个儿就是你圆坟的日子了。”杨继业咧了一下嘴,断断续续地说:“俺这么大……大个儿人参,不用酒……用酒泡着,那还不干巴?哈——”杨继业努力地想笑,但伤口疼得他咧嘴抽气。
杨继业活了,但他的腿脚一点点地发黑,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。他开始高烧,烧得胡言乱语。姜淑娥一锅接一锅熬黄豆水,不停地给他灌下去,还把水泡过的黄豆嚼碎,糊在他青紫的脚上和腿上。很快,他的双腿就黑黢黢得像烧火棍,眼看都黑过膝盖了。姜淑娥哀伤地看着男人的腿,她想不通,这么拾掇,男人血肉模糊的伤口不但没愈合,流出的脓水熏得人不敢喘气,两条腿还越来越黑。她听人讲过黑死病,据说得了黑死病的人,没有活的。老鼠的嘴有毒,咬一口就能致命。姜淑娥心陡然疼了一下,男人跌下山谷时,一定是被耗子咬了。看来男人会从腿开始死,等这病到了胸口,他就活不下去了。 一想到自己费劲巴拉地把男人救回来,可他又要走了,姜淑娥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。
“去给你爹请个郎中,好不容易把他整醒,他命再没了,咱们的日子咋过啊?”
杨石请来龙镇的殷郎中。殷郎中早就听说了杨继业的事儿,二话没说 就去了杨家。推开房门,殷郎中差点被臭气呛个跟头。他憋着气,查看了 杨继业黑紫的双腿后,沉重地叹了一口气:“锯了吧,要不命怕是保不住了。”
锯腿那天,姜淑娥把三大碗酒,灌进烧得五迷三道的杨继业嘴里,又把一块白花旗布卷起来,让他咬着。一条腿锯下来,杨继业硬是一声没吭,就昏死过去。锯另一条腿时,杨继业又疼醒了,瞪着血红的眼睛,闷哼两声,再次昏死过去。醒来,昏死;昏死,醒来——杨继业的眼睛都快滴出血来。
殷郎中早已汗水淋漓,锯下杨继业的两条腿后,他呼哧带喘地跌坐到炕上。殷郎中脸色煞白,闭着眼睛歇了一会儿,又吃了一碗糖水卧鸡蛋。吃了鸡蛋,喝了糖水,他才有力气,拿起笔开了七服汤药,还包了十几包创伤药,嘱咐道:“按时服药,按时上药。”
殷郎中出门时,脚下磕磕绊绊,要不是杨石和杨磊架住了他,他差点被门槛绊倒。送走了殷郎中,四个儿子把两截如过火木头的腿,用白花旗布裹起来,埋到前房女人的坟旁。儿子们告诉他们的生身母亲:“妈,俺爹的两条腿先来陪你了。”
姜淑娥把药汁一勺一勺给男人喂下去。
“咽下去,别糟践了啊。刚从阎王爷身边溜达一圈,咱不能再去了。阎王爷很忙,你不要给他老人家添乱。你是男人,要有男人的样儿。你在俺心里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,不能说倒下就倒下……”她像是哄孩子,又不忘讨好阎王爷。
杨继业的高热渐渐地退了下去,创口也开始结痂。除了让他喝黄豆水,女人还把烀得稀烂的黄豆捣成泥,用盐和香油拌了,给他喂下去。杨继业一点点还阳了。这天早上,他喝了女人做的蛋花疙瘩汤,使劲地吧唧了两下嘴,无限感慨地说:“阳间的饭真香啊。”他盯着姜淑娥的脸,“你瘦了,都有黑眼圈了,但还是那么好看。”
“嗯,瘦了好,身子轻松,给你翻身擦身也轻便。”姜淑娥莞尔一笑。
只剩了半截身子的杨继业,活了下来。他依旧大碗喝酒,大口吃饼子。
(未完待续)
来 源:龙江森工
责 编:卢秋影股票配资讯
发布于:北京市极速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